
1950年, 温州一老师去北京当官, 半路想起自己是汉奸, 连夜南逃
发布日期:2025-10-07 22:30 点击次数:108
1950年3月的一个阴雨夜,上海北四川路尽头传来短促汽笛声。临街咖啡馆里,瘦削书生把信封折得极整,放进内袋。外人只知道他叫张嘉仪,河北丰润士族之后,即将北上受聘。没有人猜到,真正的姓名叫胡兰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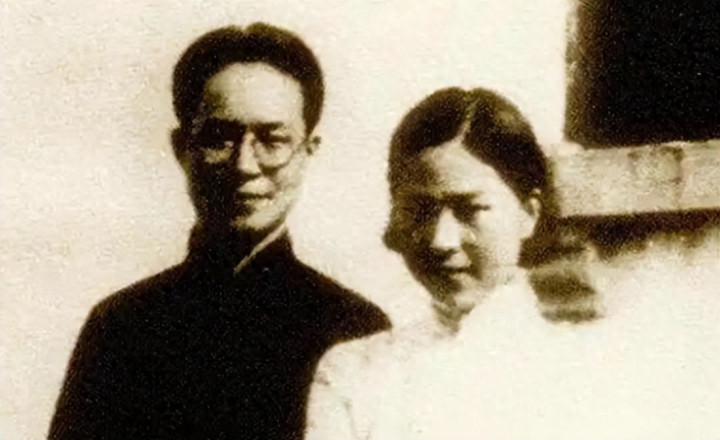
此前不久,梁漱溟在北平的住所里亲笔写信,请他参与“国家文化整理计划”。邀请函洋洋数百言,措辞恳切。温州中学的教师办公室里,张嘉仪读完信,一夜未合眼。他告诉同事:“北方需要人,我该动身啦。”口气既轻松又骄傲。
时间拨回1938年夏。上海法租界灯火稀疏,胡兰成端着咖啡,看着窗外残火。翌日,《战难,和亦不易》见报。那篇文章不提抗战,只劝“和平为上”,正合汪精卫胃口。陈璧君夸他“笔力淋漓”,《中华日报》高薪请他做主笔。胡兰成从此在伪政权里一路上扬,1940年更被汪精卫任命为宣传部政务次长。

在南京,他替日本人写稿、主持电台,还在“中日恳谈会”上讲“东亚共荣”。谷正之当面称赞,“君乃文化之桥”。听来荣耀,其实就是卖国的注脚。胡兰成暗知大势难久,悄悄为家眷另觅去处,并嘀咕了一句:“日本必败。”这句牢骚被同僚告发,他被汪精卫扣押。日本特务出面施压,才侥幸脱身。
1945年,日本投降,汪伪倾塌。战犯名单刷刷贴满街头,“胡兰成”三字赫然在列。他拎着几件旧衣,连夜离开汉口,经上海、杭州潜入温州,化名张嘉仪。靠着伪造的荐书,他在温州中学授课。课堂上,他吟宋词、讲佛经,学生觉得这位张老师文采风流。有人拜访,他总自嘲:“不过是隐居江左的散人。”

真正的算盘并未停下。1946年底,他开始频密写信给文化名流,尤其盯上梁漱溟。在信里,他引用《中庸》,自称“愿以残年投诸文化事业”。梁漱溟素重儒家同道,回信礼遇,先后往返十数封。1949年冬,梁终于写下那封正式邀请函。
1950年初春,张嘉仪离开温州。一路风顺,他在杭州小住,酒桌上被地方士绅奉为“河北遗才”。抵沪后借宿旧学生家。第三天傍晚,细雨绵绵,他步入四川北路一家旧书摊,正好听到摊主同人议论:“最近镇反,抓了好几个汪伪要员,听说名字都登报了。”摊主举起刚摊开的报纸,头版大字写着“清除汉奸残余”。胡兰成心头一紧,仿佛冰水灌顶。
他重新翻查报纸,副版有组照片,押解的几位汉奸中,旧日同僚赵毓麟赫然在列。那一刻,北上赴任的美梦碎成齑粉。他合起报纸低声嘀咕:“不能去,绝不能去。”夜色降临,他回到住处,只留下短短一句话托给女主人:“告诉梁先生,张某力有未逮,自会解释。”随即携皮箱外出,再未现身。

当晚十一点,他以假名购得船票,沿江南下,经广州潜入香港。朋友劝他:“回头自首或许还能宽大。”他只冷笑:“宽大?到时枪口前站的是我。”1950年4月,他在九龙登上一艘货轮,目的地东京。
进入日本,他重拾本名胡兰成,靠帮出版社改稿谋生,也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。课堂上偶尔有人提起汪精卫,他轻描淡写:“旧事无足挂齿。”学生看他谈《庄子》眉飞色舞,却不知道台下的资料室里,东条英机的照片旁赫然夹着他的旧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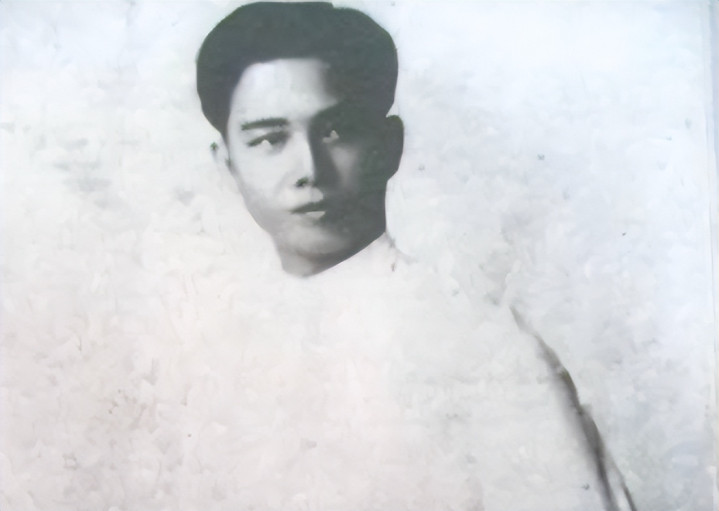
1970年代,中国对日和解,东京大学青年学者曾好奇询问:“胡先生,当年为何不回国自辩?”他回了八个字:“各人因缘,不足为外道。”对话在茶室掩埋,再无人追问。
1981年7月,东京炎热。胡兰成病危,友人守在榻旁,他突然低声说:“我本不该走那条路。”这句模糊忏悔随病榻心跳一道停息。官方档案里,他依旧属于“重大汉奸潜逃未归”一栏。

一个才子,凭机巧与笔墨走入高位,也用同样的机巧掩藏身份。历史清账时,机巧再高也罩不住真名。梁漱溟后来说起此事,只淡淡一句:“书生误我,我亦误书生。”句短,却重。
